在读完奥兰·海斯特曼(Oran Hesterman)的著作《公平的食物》(Fair Food)后,我意识到,在如何使得食物能被可持续利用的领域,他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经验的科学家。
奥兰在北加州的一个农场中长大,随后帮助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建立了一个农场,这一农场后来成为农业生态学与可持续食物系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Agroecology &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奥兰创立了一家成功的苜蓿种植企业并开始学习植物科学,最终获得了农学和植物遗传学的博士学位。在他开始参与推广可持续食物之前,他曾在密歇根州任教。他最早与家乐氏基金会合作开展这项非盈利的运动,之后又和公平食品网络进行合作。他看起来几乎了解过去20年中每一个能够改善美国食物状况的手段和代表人物。我们进行了电话采访。

奥兰·海斯特曼
我:很多试图促进食物系统向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的工作都将重心放在使人们更加了解食物的隐藏价值并为它们买单上,比如伊莫卡利工人同盟(Coalition of Immokalee Workers, CIW)就成功做到了这点。我认为,尽管我们多少都听说过这些工作,但并不清楚他们具体做了什么。那么,CIW的工作体现了哪些创新点呢?
奥兰:卢卡斯·贝尼特斯(Lucas Benitez)及其小组的工作中,有一点在很久之前我就注意到创新之处——相比于代表种植工人向种植园主索取更多的工资,他开始用一种更系统化的角度审视问题,寻求创造共赢的方法。而对他们而言,在这种共赢的方法便是让工人了解,与其把农场主视作敌人,不如大家一起做朋友。如果农场工人得到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自然会使农场更加高产。但农场主也是人,不时也会手头紧,所以他们也只“见钱行事”。
上一代的农场工人一直抱着抵制的心态工作——我想起的例子是凯萨·查维兹(Cesar Chavez)和他的葡萄。卢卡斯·贝尼特斯所做的是利用“励制”(buycott)来取代往日的“抵制”(boycott)。如果每磅番茄贵一美分——无论它们被夹在塔可钟售卖的塔克卷还是快餐店卖的汉堡里——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没太大影响。但如果工人能够得到这一分钱,那么这个价格变动将极大地提高他们摘番茄的效率。
首先,卢卡斯的小组能以更宏观的视角考虑最明显的问题,其次,他们以直接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现在你看到工人们确实得到了那一美分。
我:如果这一措施真的有效,为什么我们没见到它被推广至世界各地?
奥兰:我一直在询问自己的问题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将一个从实验中获得的对策,或者一个小小的变革加以推广?这样的推广需要你对公共政策和合作规则的变化加以考虑,因此我们必须跳出自己的小圈子来思考解决方案。此前推广本地食物和有机食物过程中的许多经验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但我们要做的比这更多。
我:好吧——让我们谈谈更深层的问题,你写到从清醒的“消费者”向关系更为紧密的“参与者”过渡,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到底要应该怎么做到这点?
奥兰:实际上每天我们每个人都在接触食物系统,因此无论我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为何,我们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如果你是学龄儿童的父母,那么你可以参与改变学校的食物状况;作为大学生,你可以联系 “Real Food Challenge”组织,参与调整食物的购买政策。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切实的机会,参与影响范围更大的政策制定。我们日前促成了一部农场法案的通过,这是很多人从未料到的。我们对本地食物的关注和兴趣已经被反映在这部法案中了,但目前意识到这点的人还很少。如果你去关注这背后所有组织所进行的努力,那么你会意识到我们所做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
我:而这是因为普通人参与其中的结果?
奥兰:是的,这正是“参与者”的力量。
我:我喜欢你关于“家长可以去学校的沙拉吧当服务生”的建议,如果有成年人的工作,孩子们应该会更乐于去吃沙拉的。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奥兰:是的。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总有一种冲动去将大量时间使用在研究上——哪里是最重要的介入点,改变现状“最有力的杠杆”又落在何处?。但后来我意识到,我最好抑制这种冲动。
我经常会想到弗雷托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话:“如果你想改变某个特定系统,你最好从任意地方开始,并遵循它的运作模式去观察系统各处。”不管是在沙拉吧还是食品系统的其他部分,只要加以关注,你就可以看到许多联系。如果保持关注和思考,我们总能发现共赢的方案。当公平食品网络最早开始发起“Double Up Food Bucks”行动(编者注:如果民众在用现金购买当地农产品时也使用“食物券”,那么政府将会进行等值补贴,让他们的购买力加倍)时,我们只是觉得这能够帮助底特律人民。而这行动最终演变为上述农场法案的一个项目,这一项目将允许以“Double Up Food Bucks”行动为先例的奖励机制推广到全国范围。
![]()

![]()
在密歇根州开展的Double Up Food Bucks行动。
我:你们在呼吁人们关注食物的真实价值方面做得很成功,成果之一是食物价格的自然上涨,但这使得人们比之前更难买到新鲜的食物。一种应对措施是政府加以资助,正如你在“Double Up Food Bucks”中所做的那样;马萨诸塞州的政府也已经开始着手资助老年群体购买新鲜食物。你认为“政府出资替低收入群体购买食物”是一项应当长期推广的政策吗?
奥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大家都较一致地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保障安全的网络,使得人们在遭受失业或疾病时仍能正常生活。我们建立的第一个与之相关的网络是SNAP(补美国补充营养协助计划,也被简称为“食物券”制度),这使得家庭能够免受饥饿折磨。但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花时间建立起一套系统,使得系统中贫困人群所在地区的邮编与难以获得物美价廉的食物的区域邮编相一致。这样,我们在采取介入措施使这些家庭得以利用食物券获得更多蔬菜和水果的同时,那些资金也被用来扶持农民和资助当地的食品经济。我们将我们的这个项目视为解决饥饿、居民健康问题和本地经济发展问题的综合项目。
我:事实上它有效果吗?有证据表明提高食物的获得力并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这就好比在食物的荒漠上开一家食品杂货店。
奥兰: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93%的SNAP参与者都表示自己吃到了更多的水果和蔬菜。83%的参与者的表示他们更少的摄入高脂肪食物。因此我们认为这一项目收效良好。你确实不能只在沙漠中放个食品店就期望变化能够发生,你还必须为你所希望实现的变化创造机会。拿密歇根州为例,如果本地的食物状况改变了20%,那么我们就可以创造出42000个就业机会,并带来30亿美元的总经济效益。
我:你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健康的食物循环,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并让民众在农产品市场购得更多的食物。但是耕地的情况又怎样呢?你曾指出可持续种植和有机农业存在不同,能否解释这一差异?
奥兰:我觉得我所在城市安娜堡(Ann Arbor)地区作为例子最合适了。利用地方财产税,我们保护了城市近郊数千英亩的耕地免于被开发。但这并非全部,我们同时保留其中的部分土地供下一代的农民种植,以可持续的耕作方式种植作物供应本地市场。
这是纯粹的有机农业吗?有些是,有些不是。但是这些年轻的农民正更少地使用农药,学习堆肥、种植覆盖作物、轮作的知识,也学习通过混栽的方式保护益虫。我们不止是留出空地,同时也在以多产的方式种植食物提供给本地市场。这些年轻的农民主要购买商是本地的市场和餐馆。此外,我们还将建立一个食物集散中心来保证本地食物的供应和分配。
我:这听起来像是在说,如果想做真正对耕地有益的事情,与其立法设定严格的规则勒令农民遵守,不如对他们加以支持并为他们留出所需的空间。
奥兰:是的,并且我们希望这能给农民带来更好的生活。我们曾认为提供直接售卖是提高本地农民生活水平的唯一手段,但我现在对此表示怀疑。建立直接的售卖关系,农民将作物卖给农产品市场、社区互助农业机构或餐厅确实不失为一种好办法,但并不能推广到区域性食物系统的层次。我们需要支持那些在分配链中的企业——这些企业有能力从农民手中购买作物,将食材带到学校、研究所、医院、商店或是餐厅。我认为这个关节蕴藏着巨大的机会和迫切的需求。就此,我们正展开一个名为“公平食品基金”(Fair Food Fund)的项目,为这类企业提供资助。
我:可以举例说明么?
奥兰:在缅因州,有13家生产乳品的个体户因为距离城市太远被他们的牛奶经销商放弃了,因为对经销商来说长途跋涉到农村地区取牛奶是不实际的。他们没有就此停业,他们共同成立了一家叫做“缅因本地有机牛奶”(MOOMilk)的公司,并与卡车公司签订合同,让卡车来收集牛奶。他们目前在波特兰设有装瓶车间,牛奶包装到纸盒后辈运送至新英格兰各地出售。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需要更多的奶牛来扩大公司规模。公平食品基金便资助了一个贷款计划。
我:所以你们被需要的原因是?这不就像是老式银行那样提供借款么?
奥兰:对这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和小个体户来说,要从银行取得资助是不太可能的。要注明两点:一是我们的借款方式与常规的银行业务是不同的;二是我们要意识到,食品行业存在联合,银行业自然也存在联合,这使得在农村地区,会与社区保持紧密联系的银行少之又少。我们了解到,国家银行通常往往很难了解本地社区的发展,因此他们不会贸然资助像MOOMilk这样的企业。
我:你在书中描写与“可持续食物实验室”的第一次会晤的场景让我觉得似曾相识。曾有非营利性组织的领导人扬言称大量的食物会毁掉一切,这使得企业家们鄙夷地指责他们在全球正有大量人饿死的时候还只知道盯着自己的有机食物。
奥兰:有时谈起可持续农业,人们就会快速“站队”。但幸好那是与可持续食物实验室的首次而非最后一次会议。那些人总在喋喋不休。但我认为情况正在变化。我理解你描述的那些“熟悉”的场景。但是我想告诉你,数周前沃尔玛公司与CIW签订了一项协议,这协议正预示着事态是怎样开始变化的。这项协议并不那么关注大企业与小企业、常规农业和有机农业之间的矛盾——他们更关注的是双赢的思路和办法。当你开始为此行动时,那条区分不同意识形态的线将开始消融。
我:从争论的人口中冒出的“我们对抗他们”一类的雄辩辞藻我听得多了,但如果我们能够身体力行去商量寻求更好的办法,我同意,意识形态会慢慢变得不再是问题。
奥兰:所以我想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如果我们将更多时间花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并努力让解决对策得以实施,而非在区分意识形态上花时间,我们也许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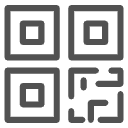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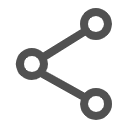
评论